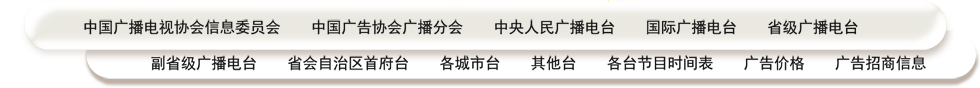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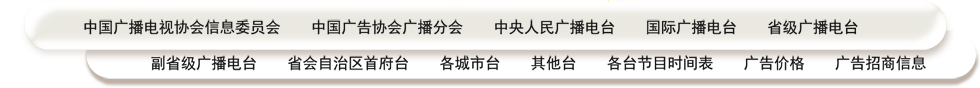
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受人际间沟通的影响很大,而消费特征处于形成期的青年人尤为如此。结合中国青年人的消费社会化和品牌购买行为,建立了社会沟通影响青年人品牌忠诚的概念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发现:青年人主动与父母沟通有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青年人被动与父母沟通无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青年人与朋友沟通有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网络沟通对青年人品牌忠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是社会沟通影响青年人品牌忠诚的中介变量。
一、引言
近年来,探索青年人品牌忠诚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从社会沟通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是一个独特视角。关于社会化执行主体对青少年消费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各社会化执行主体作为独立因素对青少年消费的影响研究上。研究发现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社会沟通与青少年的媒体使用、购物的独立性以及他们意见的认同性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社会心理学家希曼等提出了参照理论认为每一个体都会用某一团体的规范来对照自己的言行,这个团体就是该个体所要尽力使自己的言行与其规范相一致的团体。通过这个群体理论及其相应的社会化作用的研究,可以对同龄群体影响做出解释。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将网络媒体作为人际认同的一种手段,会影响到他们将要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机会。可以看出,青少年与家庭、朋友以及网络之间的社会沟通会对其品牌忠诚构成一定的影响。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社会沟通对青少年品牌忠诚的影响,并对其加以应用,来增加销售收入。就网络社会沟通对青少年的影响来说,众企业越来越认识到了网络媒体的巨大作用,一些新兴的企业如凡客、梦芭莎、兰缪等更是将网络广告的作用充分发挥,通过著名网站的嵌入式广告,广告邮件,众论坛和贴吧中的广告贴等对青少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使人感觉它们无处不在,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综上所述,理论和案例均表明青少年的三种社会沟通——家庭、朋友以及网络媒体沟通都对其品牌忠诚构成了影响。但是,这一结论需要通过实证进行检验。本文便试图来验证这一重要问题,并将重点放在社会沟通对青年人品牌忠诚的影响上。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家庭对后代社会化的影响常被称为“代际间的影响”,内容包括个人的规范、态度和价值。凯勒(Keller)认为从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概念来看,代际影响实际上是品牌资产的一种重要来源。还有些学者认为,当提到消费行为的时候,父母作为一个社会化主体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些模范者、老师或者社会中的一般人士在父母亲态度的传播过程中已经被过滤掉了。一般来说,父母与孩子对消费行为及购买商品后的态度交流得越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家庭中父母的权威性越高,孩子对父母越尊重,代际影响就越显著。
除了来自家庭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朋友之间的沟通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影响对象包括对消费重要性和消费品牌的认同度等。艾略特和莱纳德(Elliott and Leonard)在调查中发现,青少年总是穿着与其朋友相似品牌的运动鞋,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交际。道特森和海特(Dotson and Hyatt)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来自朋友之间社会沟通的影响,会随着个体的性别和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女孩更倾向于因朋友的使用认同一个品牌,而男孩更倾向于因品牌本身存在时间的长久性认同一个品牌。巴哈曼、黛博拉和阿克什(Bachmann,Deborah and Akshay)的研究证实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对于一些公开性的消费项目同龄群体之间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而对于一些私密性的消费项目同龄群体之间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体的形式越来越多且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麦克尼尔和麦迪(McNeal and Mindy)探讨了小学生在信息获取当中各因素的影响力,发现个体在有意识无意识中接触到的媒体作用高于家庭、朋友的影响,并指出电视在其中起着最大的作用。同时网络的使用在青少年当中迅速的扩张。克里斯蒂娜、丹尼斯和塞西莉亚(Christina,Denise and Cecilia Hii)通过一系列的访问和调查发现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已不仅仅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而是已经扩展到了网络。
可见,学者们就青少年与父母和同龄群体社会沟通对其消费行为影响研究已经较多,但大都局限于在一个时点上各因素对青少年消费行为影响的定性或定量研究,而没有将其纳入到一个整体模型中。同时,在媒体社会沟通方面,现有研究多局限于研究一般媒体的作用,比如电视、报纸等,但如今网络在青少年生活当中的比例已逐渐增大,故研究网络沟通对青少年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显得很有必要。
三、研究假设
建立从理论逻辑上分析,父母、朋友、媒体等社会沟通会使青年人对企业品牌产生联想,形成一定的品牌形象认知,从而影响其品牌忠诚。首先,父母、朋友、媒体等社会沟通会使青年人对企业品牌产生联想,并形成品牌形象认知。沃德(Ward)、布里(Br6e)、马斯卡仁(Mascarenha)在研究青少年购买行为社会化时指出,青少年会在父母、朋友、媒体的影响下产生品牌购买行为。青年人在与家庭沟通时又分为主动沟通和被动沟通,而这两种模式对青年人的品牌认知也不同。同时,结合现阶段青年人的媒体习惯,本文认为,媒体沟通主要表现为网络沟通。这样,与家庭的主动沟通、与家人的被动沟通、朋友之间的沟通、网络沟通就构成了当代青年人沟通的主要模式,而这些主要模式有可能影响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和对品牌形象的认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与父母主动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呈正相关关系;
H1b:与父母主动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关系;
H2a:与父母被动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呈负相关关系;
H2b:与父母被动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形象认知呈负相关关系;
H3a:与朋友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呈正相关关系;
H3b:与朋友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关系;
H4a:网络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呈正相关关系;
H4b:网络沟通和青年人的品牌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及对品牌形象的认知可能影响其对品牌的忠诚。品牌联想、品牌形象和品牌忠诚均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者关系上,凯勒(Keller)、斯佩罗和斯通(Spero and Stone)、范秀成(2000)、何佳讯(2006)等人展开了大量讨论。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青年人的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的认知对强化其对企业品牌的认知,最终形成对品牌的忠诚与否。据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5:青年人的品牌联想与品牌忠诚呈正相关关系;
H6:青年人的品牌形象认知与品牌忠诚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社会沟通对青年人品牌忠诚影响的概念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封闭式问卷,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测试被调查者的品牌选择,让被调查者在耐克、蒙牛、统一等诸多品牌中选择一个。第二部分测试被调查者对已选择品牌的忠诚度。第三部分测试被调查者消费已选择品牌过程中的沟通情况,分别为家庭主动沟通、家庭被动沟通、朋友沟通和网络沟通。第四部分让被调查者填写其基本信息。问卷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在对问卷进行预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正式调查于2011年3-4月在北京等地展开,先后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100份,有效问卷558份。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1所示。

(二)量表开发与检验
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研究所需要的变量。社会沟通变量设计主要参考沃德(Ward)、布雷(Brée)、马斯卡仁(Mascarenha)等人研究青少年社会沟通所采用的量表。品牌联想、品牌形象认知、品牌忠诚等变量主要参考艾克(Aaker)、凯勒(Keller)等人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对原有量表进行了改进。同时,为了保证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在北京进行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修改了测量项目,形成最终的测量量表。
首先,在信度方面,每个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在0.731与0.901之间,都大于0.7(见表2),表明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了较好的拟合指数。

其次,在效度方面,各变量因子载荷大多大于0.6(只有少数几个未达到这一标准,但接近这一标准),且有较好的解释方差百分比,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检验量表的判别效度。结果显示判别系数较好。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方法检验所涉及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该方法可以检验测量模型(即验证性因子分析),也可以对理论模型整体结构进行检验。同时,该方法属于一种多元统计技术,其自变量和因变量既可是连续的,也可是离散的。
五、实证分析
(一)SEM模型分析
运用SPSS 16.0和AMOS 17.0对概念模型进行了数据拟合。该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df=6.204,GFI=0.805,NFI=0.757,IFI=0.788,在基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存在优化的空间。本文进一步对路径进行了修正,在SEM模型中去掉“网络沟通”变量,重新建立SEM模型,得到修正后的拟合模型,如表3所示。修正后的拟合指标为χ2/df=7.105,GFI=0.813,NFI=0.762,IFI=0.788,拟合效果有所改进。可见,假设Hla,Hlb,Hla,H2b,H3a,H3b,H5,H6得到证实,H4a,H4b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实证分析表明,青年人主动与父母沟通这一模式会使青年人对品牌形成良好的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从而形成品牌忠诚;青年人被动与父母沟通会使青年人形成较差的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从而无助于品牌忠诚的形成;青年人与朋友沟通这一模式会使青年人对品牌形成良好的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从而形成品牌忠诚;网络沟通对青年人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乃至品牌忠诚,均没有显著性影响。
(二)中介效应分析
按照伯龙和肯尼(Baron and Kenny)的观点,本文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了估计。
图2表示的是实现相关条件的统计结果。在这四个条件下,只有品牌形象认知不是与父母的主动沟通和品牌忠诚之间的中介效应,其他的均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是社会沟通影响品牌忠诚的中介变量。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经实证分析,社会沟通对青年人的品牌忠诚的影响表现在:青年人主动与父母沟通这一模式有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青年人被动与父母沟通无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青年人与朋友沟通有助于品牌忠诚度的提升;网络沟通对青年人品牌忠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本文发现,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是社会沟通影响青年人品牌忠诚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青年人品牌忠诚的形成,有赖于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的形成,而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的形成受社会沟通的影响。
以上结果与中国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一般而言,由于青年人与父母存在一定的代沟,父母若经常干扰青年人的品牌购买行为,容易形成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反而对父母建议的品牌形成较差的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相反,若青年人主动向父母征求品牌购买建议,说明青年人比较相信父母在这一方面的经验,而在感情纽带的作用下形成较好的品牌联想和品牌认知,提升了青年人的品牌忠诚度。同时,青年人与朋友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认知偏好,容易在沟通中形成共鸣,故朋友沟通这一模式会使青年人对品牌形成良好的品牌联想和品牌认知,从而形成品牌忠诚。但是由于中国网络喜欢炒作品牌方面的负面新闻,而青年人一般也不太相信网络上的宣传,故网络沟通对青年人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乃至品牌忠诚,均没有显著影响。
(二)展望
虽然本文探索到品牌联想和品牌形象认知是青年人品牌忠诚的中介变量,但青年人品牌忠诚的形成机理还需进一步探索。一方面,理论上需进一步分析青年人品牌忠诚形成中的关键变量,完善青年人品牌忠诚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另一方面,实证上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提高实证分析中的科学性,使用多种统计方法检验青年人品牌忠诚形成机理
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编:孙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