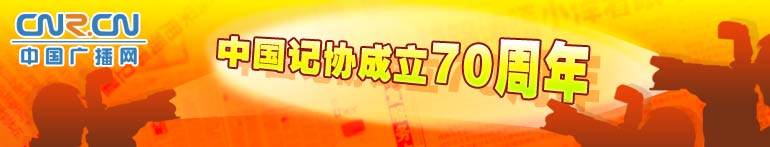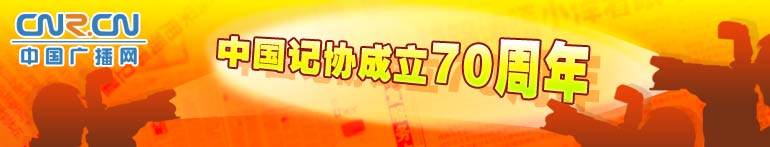|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菲
“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人生即选择。”这是我对生活的理解。而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迷茫,也就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择。当他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我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节目中,我把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演绎出来,做成小广播剧,或者直接现场连线,让嘉宾亲自讲述曾经经历的选择。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跟着主持人一起面对主人公人生中的十字路口,就比如在一个婚姻中,是应该继续生活还是分开,先让大家琢磨,然后再用主人公真实的例子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做的,演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而新的情况又变成了什么样的十字路口,他又是怎样抉择的。经过两三个关口之后,主人公的人生呈现在听众面前,让大家了解每个选择带来的结果,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的结局。听众经历了、参与了,他们自然就会去想,去思考,等于给大家一些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在每个十字路口,我都会给听众分析“选择”背后隐含的道理和感悟。这样互动的形式特别贴近受众的需求,无形当中,也给听众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主持人是一个懂得“选择”的人,是一个有能力指导别人如何选择的人。
其实在《神州夜航所以生活》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辜三(辜海军)就很碰巧地听到了。1993年,在家乡一个小厂里,19岁的辜海军因为一双拖鞋与工友发生争执,将对方致死后畏罪潜逃,被公安部网上通缉。辜海军小学没有毕业,看不懂报纸,每天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让他更没有条件看电视,他获得信息的唯一途径就是听广播。
夜深人静,当辜海军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他听着广播里主持人讲述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分析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每一个人生十字路口该如何正确选择,以此来不断地告诉听众“走好人生路,关键就几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节目的形式,让他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困境:徘徊在自杀与自首的人生十字路口,无从选择;而节目中主持人亲切的声音与真诚的话语赢得了他的认可与信任。
2005年2月4日23点38分,辜海军鼓足勇气给我发来了一条求助短信。他说:“向菲姐,您好,我是一名罪犯,因过失伤人,正四处逃亡,现在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望提醒一下……” 这时,离我的直播节目开始的时间0点10分还有近二十分钟,我仔细地分析了短信的内容,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名《神州夜航》节目的老听众,因为《神州夜航》有多个主持人主持节目,他能够在我还没有开始主持节目、开口说话之前,就知道今晚是我主持节目,证明他对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和主持排班非常熟悉。另外,他的“犯罪行为”应该已经立了案,否则他不会用“罪犯、过失伤人”等这样一些专业术语,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现在不想“逃”了,否则,他不会发这样一条既能显示手机号码又能显示他逃逸地点的短信。在这条短信中,我读到了一份对我的信任。
“他是我的听众,他需要我的帮助,我必须帮他。”当时心里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这种事情,我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短信所述确有其事,那么我也许会成为他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人,同时,我更想通过告诉他我的私人手机号的方式,给发短信的人传递一个信息:谢谢你信任我,我回馈一份真诚帮助你的心。我马上示意导播按短信显示的号码打回去,让导播告诉对方,节目结束后可以跟我联系。
主持当天晚上的直播节目时,我确信,此时此刻,躲在某个角落里的那个发短信的人一定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我想,他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条短信,他是在投石问路,验证我的可信度,我的一言一语稍有不慎都会让他重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所以在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中,我没有提及这条短信,唯一刻意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节目结束前,就着当晚的节目内容,说了这样一段话:“收音机旁其它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也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如果你也面临选择的困惑,希望你把向菲当成你可以信任的朋友,我来帮助你。”没想到,这句话还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辜海军在自首后对我说,当时他发出短信后,非常后悔,心里很矛盾,当他听到我在节目结束时说的话,他想了整整一夜没睡觉。天亮后,他决定相信我。
第二天上午十点,辜海军用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给我回了电话。从这之后,辜海军晚上就听我的节目,白天我们在电话里交流。
在电话里,他说朋友叫他“辜三儿”,我没有追问他的真实姓名;他提到家乡的趣事,我没有追问具体地址;他不想留自己的联系方式,我告诉他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等着他的电话……所有他不想让我知道的信息,我都避而不问,辜海军的警觉慢慢的消失了。当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他只说了两句话,我就听出他是四川人,他放松了,因为他聪明地意识到,我是很认真地在倾听他说话,他现在正是需要一个能够认真倾听、真诚待他的朋友。他说自己在逃亡途中做了哪些好事,我像夸自己的小弟弟那样对他给予肯定,当他身上存留的自尊与善良,得到了心目中“强者”的认可时,他感动了,而感动恰恰最能够把人们看起来已经泯灭的良知激发出来。
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对辜海军正面说出“自首”这个词。我觉得我更需要做的是,让他鼓起对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我要让他自己发自内心地做出自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勇敢地面对自首后所要面临的法律的审判。
大年初三,辜海军在电话中第一次坦言,他要自首,并且希望我能陪着他去自首。作为一个潜逃了近12年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他对警方恐惧心理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他需要有个他信任的朋友陪他迈出人生中关键的一步。2月16日,我与辜海军失去了联系,当我们再次联系上时,他已经站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2月17日,我陪同辜海军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自首。
2月22日凌晨,辜海军的故事被制作成一期特别节目在“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播出,题目就叫《抉择》。一时间,听众反响热烈。也有不少人声称要自首,但很多号码是经常参与节目的,一看就是恶作剧。
但真的还是来了。
2005年3月24日深夜,我和往常一样做着节目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节目将在零点10分播出。直播前半小时,23点34分,短信平台上出现了一条短信:“向菲姐,我也要走孤(辜)三的路,站(暂)不要告诉别人。”与辜海军有条不紊的短信不同,这条短信别字连篇。当时看到这条短信,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深信在我的听众中,肯定有与他类似经历的人,辜海军绝不是唯一。我依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做完节目后记下了这个手机号码。第二天上午10时,我给对方回了一个短信:“你好,我是向菲,你好端端的干吗要走辜三的路啊?”
一小时后,对方回信:“向菲姐,我上演了一部武松传!”
“武松传?!”我感觉里面有问题,很快又给对方回了一条短信: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扮演历史人物可不容易,你怎么当了武松呢?你是武松啊,还是武松传里的其他人物啊?
我并不想急于探究对方,但对方明显很急。20多条短信往来后,这个自称“袁国栋”的人觉得短信里根本说不清楚,他想和我通电话。
3月26日上午10点,我在家中接到了电话,对方带着很浓重的陕西口音,我也开玩笑地跟他学说陕西话。他说他现在说话不方便,约定晚上8点以后给我电话。
跟辜海军不同的是,袁国栋晚上的这一通电话打得时间很长,近四十分钟,而且声音特别大,有时大得让我不得不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远的。显然,对方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我甚至听到了类似蛐蛐的叫声。我能感受得到,他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痛快地说话了,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可以放心说话的人,就急于把憋在心里、压抑许久的话统统说出来。
袁国栋学名袁炳涛,家住陕西省礼泉县。2001年11月,袁炳涛杀人后逃跑。
袁炳涛在电话里告诉我,逃亡期间,他很痛苦,痛苦地连哭都不能哭。一个大男人,如果流眼泪,人家会觉得很奇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想哭的时候他就躲到野地里面,放声大哭,哭得痛痛快快之后再回去。这样宣泄之后可以保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再去野地里哭。日子久了,每隔一周在野地里的痛哭已经缓解不了这种压抑,他极需一个可以倾吐他心声的渠道。他告诉我说,去年开始,他喜欢上了听广播。一个简易的8元钱的收音机,成为他生活中的好朋友。白天干活时,他把收音机挂在树上,边干活边听,到了晚上,更是需要靠听收音机来打发孤独寂寞的时光。他说,特别想发短信参与节目,为此特意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部破旧的手机,每到节目开始时,他就开始编写短信,但是因为手机太过陈旧,等他编写好了几十字的短信,我已经在节目中向听众朋友说晚安了。3月24日他发给我的那条求助短信,是早在白天就提前编写好的。
在和袁炳涛通话的过程中,我经常暗暗拿他与辜海军对比,同样希望自首,袁非常坚定,辜略显犹豫。还有一个明显不同,辜海军基本是在正常情况下打电话,而袁炳涛却是不分时间和地点,他渴望交流的愿望更迫切。在后来的通话中,我明显地意识到,袁炳涛不仅仅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了,他还需要对方对他的选择给予肯定。我需要像鼓励辜海军一样,鼓励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我跟他谈父母,谈家乡的果园,谈他日思夜想的女儿,谈自首后,他将面对的生活。袁炳涛由一开始的倾诉者变成了倾听者,也正是因为前期我真诚地倾听他的诉说,才能让他此刻愿意听我说话。
3月31日凌晨6点多,还在睡梦中的我,又一次接到了袁炳涛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不能再等了,要求我陪着他去自首。4月1日,袁炳涛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带警察来呀?”,我说:“你让我陪你自首的,我为什么要带警察来呢?”这时,我从他的眼中读出了被人信任的感动。
一个真诚的声音能让逃犯悔悟,逃犯真诚的声音能让另一个逃犯结束逃亡生涯,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事隔七个月后,在这个“多米诺”里又多了一张“牌”。
他叫余昭明,六年前因与妻子发生口角,将妻子误伤致死后潜逃。余昭明的情况与辜海军、袁炳涛完全不同,他不是我的听众,他是看了一期电视节目知道的我。也因为不是听众,没听过我的节目,他对我毫无信任可谈,但是他又需要一个可以听他说话,帮他拿主意的人。所以余昭明在我身上用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来“考验”我,整整“考验”了十三天。最后,我通过了他的“考验”,他9月18日中秋节到北京投案自首。
他先考验我的责任心。发了一条比较醒目的短信到我的手机上:“我要求你帮帮我生死路”。而我是本着不管我是否能帮得上你,我都应该礼貌负责,我给他回了短信,我们取得了联系。
接着他才用各种方式考验我对他的诚心。他会在电话里故意告诉我他现在在某个城市某个大桥的第几个桥墩子下面,后来发现,并没有出现他想象的景象。从跟我通电话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几个城市之间,后来他发现并没有警察后脚跟着去找他。他明白,我是真诚对他的。
他又考验我的耐心。他打电话是从不分时候的,凌晨2点,3点,4点,如果你没接着,那他就三、五分钟打一个。他打电话从不论时间长短,最长一次通话达到了近四个小时。
他亲自考验还不算,他还搞“市场调查”。他给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给第二个案犯家属打电话,一个目的,想听听这些人是如何评价我的。
而他惹我生气、发脾气都是故意的,这是我没想到的,直到他投案自首后,我看到了一期他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我才知道他那也是考验,想考验一下我是不是真为他好,按他的理论,一个人如果在生气状态下还在想着为对方考虑,那他就是真为他好。最终,我的不放弃换来了余昭明的放弃,他放弃的是继续逃亡。
我常常在想一个比喻:辜海军、袁炳涛、余昭明就像是一壶即将烧开的水,他自首的念头其实已经烧到了99度,而我只是又拢了一把火,给了他们欠缺的1度,烧开了这壶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名站在第一线与听众最贴近的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我必须要具备随时随刻准备送出这1度的社会责任感。这1度也许会使一段友情失而复得;这1度也许会挽救一个濒临破裂的家庭;这1度会改写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消除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比如辜海军和袁炳涛。回头去想,这三名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其实他们在社会上是有不稳定性的,如果他们没有投案自首,他们就是社会的隐患。通过这三件事情,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我的听众,我的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也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